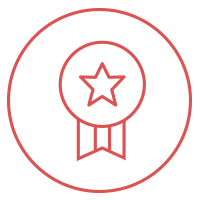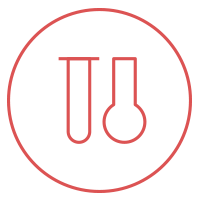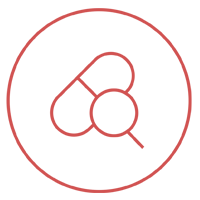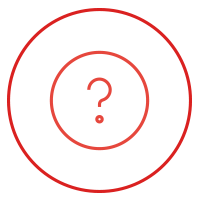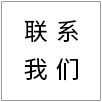(黑龙江)【以法为教,筑牢防线】全省体育系统开展《刑法修正案(十一)》学习
2021-01-19
背景
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明确将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是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又一里程碑,对提升反兴奋剂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公布后,黑龙江省体育局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要求全省各地市体育局以及所属运动队做好深入贯彻落实,以刑法规定兴奋剂入刑的相关内容为主要抓手,迅速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持续强化反兴奋剂意识,形成警示、震慑作用,确保人人知晓、人人掌握。
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分别认真组织专题学习并开展讨论,全省共计3218人参与专题学习,实现了项目、人员全覆盖。大家一致认为,涉兴奋剂违法行为“入刑”,表明了我国对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对保障运动员干干净净参赛至关重要。

兴奋剂“入刑”,无疑将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威慑力度,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兴奋剂问题,用法治护航干净奖牌、纯粹体育,这也意味着“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逐渐成形并发挥威力,同时也要正视短板、排除风险,以确保中国运动员干干净净参加各类赛会。

构成犯罪的行为有了刑法依据
2004年,国务院颁布《反兴奋剂条例》,规定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组织、强迫、欺骗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规定违规的运动员、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受到相应处罚,如禁赛、罚款、行政处分等,对非法生产、销售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企业可以没收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修正案》新罪名的增设,则精准回应了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表示,《修正案》新罪名的增设在处罚体系、责任体系上进行了对接,使得“构成犯罪的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再是“稻草人条款”,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刑法依据,实现了反兴奋剂的“行刑衔接”。
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
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在运动员面前鼓吹使用兴奋剂的好处以刺激、诱使他们使用兴奋剂,或者示范、示意运动员使用,甚至编造虚假事实,暗地里在药品、食品中掺入兴奋剂,使运动员不知是兴奋剂使用,都涉嫌违法。要明确的是,对于引诱、教唆、欺骗的对象,一般应当是从未使用过兴奋剂的人,或者曾经使用过但已停止使用的运动员,如果运动员一直在使用兴奋剂,便不构成引诱、教唆、欺骗,有可能属于非法提供。另外,明确刑法评价的体育活动范围,即“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运动员之间、运动员父母,以及其他任何人明知运动员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实施上述行为,都构成犯罪。不过新增罪名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对于兴奋剂误服误用不属于刑法制裁对象,尤其对于“不明知”运动员参加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的行为,不构成本罪。
对兴奋剂违法行为实行全链条打击
相比2020年1月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来说,本次发布的《修正案》与其为相互补充的关系,并且在《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司法解释》是在已有的罪名基础上进行解释,找出适用涉兴奋剂违法罪名,比如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组织他们在体育运动中非法使用兴奋剂,可能会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定罪处罚,但如果面对的是成年人就无法适用这些罪名。《修正案》明确将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实现了入罪化,实现了对涉兴奋剂犯罪的精准打击、要害打击。
此外,《修正案》与《司法解释》一起,对兴奋剂的走私、非法经营等源头行为,和非法提供、引诱、教唆、欺骗使用等行为,实现了全链条的打击。《修正案》出台后,还需要出台司法解释或者行政立法对一些概念进行明确来指导司法实践。例如怎样定义“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再比如赛外检查,尤其是赛前准备阶段内发现相关行为是否属于新罪名的评价范围等。
< 上一篇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