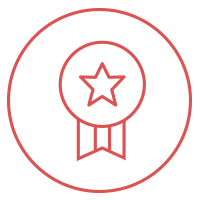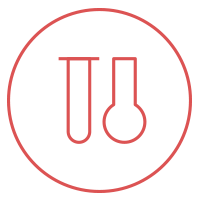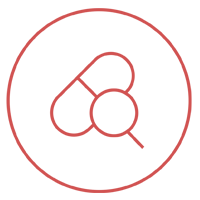国际奥委会与反兴奋剂斗争
2010-05-25
回顾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历史,说起反兴奋剂斗争,首先要提及的体育组织就是国际奥委会(IOC)。毫无疑问,没有国际奥委会,就没有国际反兴奋剂斗争。
高举反兴奋剂大旗
参加体育比赛的选手使用兴奋剂虽然“远源流长”,并且在近代和现代更为流行,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一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基本上属于无人过问的“用者自用,知者无奈”的状态。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率先高举反兴奋剂大旗,坚持不懈地在世界体坛进行反对服用兴奋剂的斗争。作为奥林匹克运动道德观的坚定护卫者,国际奥委会不仅在4年一次的奥运会上,而且在世界各种类型的体育比赛中都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
为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减少和消除体育运动中滥用药物的丑恶现象,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医学委员会的体育组织。1961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成立于希腊雅典。1964年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小范围的试验性兴奋剂检测。多年来,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一直担当着国际体坛反兴奋剂先锋的重任。
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者,国际奥委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兴奋剂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任务,例如在奥运会上实施反兴奋剂检查、召开各种国际反兴奋剂会议、考核并批准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公布体育运动中的禁用物质与方法名单、协调各运动项目国际联合会对滥用药物运动员的处罚标准,建立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出资成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已经面临道德危机的当代体育运动进行道义上的领导。一言以蔽之,40多年来,国际奥委会为奥林匹克反兴奋剂斗争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下面让我们从奥林匹克运动漫长的历史中,寻找国际奥委会留下的反兴奋剂足迹,看看它所发挥的重要领导作用。
历史回眸,承担重任
竞技者通过使用药物来增强体力和刺激精神的事古已有之。而近代体育运动中使用可提高成绩药物的更是大有人在。1896年现代奥运会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中叶,已有关于比赛选手服用兴奋剂的报道。1865年,在荷兰的一次游泳比赛中发现有选手服用兴奋剂。1879年,又有关于自行车运动员在六日赛中服用兴奋剂的报道。
在1908年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多兰多·彼得里跑到终点后昏迷,被认为是服用了刺激剂士的宁。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士的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仿,滥用药物之风愈演愈烈。1952年挪威奥斯陆冬季奥运会举行滑冰比赛时,赛场工作人员发现,运动员更衣室中到处扔着用过的空药瓶和针管,一片狼藉,景象可怖。
促使国际奥委会痛下决心的时刻终于来临。1960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在进行公路自行车比赛时突然死亡。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衰竭致死。翌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成立于希腊雅典,由阿瑟·波里特爵士出任主席。1964年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试验性地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几种药物的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兴奋剂检测。三年之后,阿瑟爵士辞职,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重组,由比利时的亚历山大·德梅罗德亲王担任主席。正是这个由德梅罗德领导的医学委员会,在1968年的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查。
进行兴奋剂检查必须有禁用药物名单,国际奥委最早提出禁用药物名单是在1967年。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于1968年初在第10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前,正式宣布了专为法国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兴奋剂检查制定的禁用药物名单。当时的禁用药物种类不多,仅包括:①拟交感胺类(例如:苯丙胺)、麻黄素及类似药物;②中枢神系统刺激剂(士的宁)及兴奋剂;③麻醉剂和止痛剂(例如:吗啡)及类似药物;④抗抑制剂(例如:IMAO)、丙咪嗪及类似药物;⑤强安定剂(例如:吩噻嗪)。
此后,1968年7月,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会议,讨论、总结了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首次正式实施兴奋剂检查的经验,并提出了将继续在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进行反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的方案。其中对兴奋剂物质的补充说明如下:
如果使用了无营养作用,但却能靠其成分或剂量刺激人体能力的药物,即使是用于治疗,也将被看作为使用了兴奋剂。特别是以下药物:①拟交感胺类(例如:苯丙胺)、麻黄素及类似药物;②中枢神系统刺激剂(士的宁)、兴奋剂及类似药物;③麻醉止痛剂(例如:吗啡)、美散酮及类似药物。
实行药物检查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同日益增多的滥用兴奋剂现象做斗争。据调查,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滥用兴奋剂最严重的依次为自行车、田径、举重、游泳。
1967年,英国著名自行车运动员汤米·辛普森在环法赛途中死于法国境内6000英尺高的旺图山峰。当时,因极度衰竭而神志昏迷的辛普森,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人们在调查他的死因时,发现他的血液中含有苯丙胺,而且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和旅馆房间里也发现了没有服用完的苯丙胺。辛普森的死为自行车运动敲响了警钟。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国际自行车联盟(International Cycling Union)领先于所有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率先开始禁用据信可提高成绩的药物。后来,在国际奥委会的协助下,其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效法国际自联,陆续开始禁用所谓的可提高成绩药物。
由于检测手段的提高,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服用苯丙胺等药物的运动员就已明显减少,正如英国奥林匹克协会主席阿瑟·戈尔德所说,只有那些粗心大意或没有头脑的运动员才会在兴奋剂检查时被抓住。国际奥委会,特别是其医学委员会下属的兴奋剂分会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其实是激素类药物的使用。这类药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运动员广泛使用。1973年,前奥运会链球冠军美国的海尔·康诺利承认:从1964年至1972年,作为他的投掷训练的组成部分,他像他的所有竞争对手一样,一直在使用合成类固醇。
类固醇检测难题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预见不到合成类固醇会有那么广阔的应用范围。最初,仅认为只有田径运动的一些投掷项目、举重以及搏斗项目中的那些重量级运动员,才有可能靠增大肌肉块头获益。然而,其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发现,合成类固醇能使他们在大运动量训练后更快地得到恢复,而且许多项目的运动员——从长跑到游泳,从短跑到自行车——都可从中受益。
说起激素类药物,头一个难题就是检测问题。在这一点上,国际奥委会非常感谢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雷蒙德·布鲁克斯教授,他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可靠的分析方法。1974年,在新西兰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采用这种方法进行了检测分析。国际奥委会对使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科学检测结果感到满意。于是,1975年4月,国际奥委会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有8名举重运动员药检结果为阳性,其中7人被证实使用了合成类固醇。
但是,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在1976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阿诺德·贝克特教授指出:“运动员可以在训练时服用合成类固醇,然后在某个预定的比赛前一星期左右停止服用,这样他比赛时就至少可以保持着服药带来的力量优势,但检测比赛后采集的尿样时又显示不出阳性结果。即使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决定在全年的各种比赛中进行随意抽查,充其量也不过是给运动员连续服用合成类固醇的日程安排造成一些困难,顶多起一些威慑作用。”
可惜的是,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人想到和提出由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建立赛外药物检查制度的创议。据统计,截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在夏季奥运会的主要赛项田径项目中,世界各国已记录下了140多起药物违禁案例,其中包括许多奥运会冠军或世界纪录保持者,而许多服用禁药的事件都发生在本·约翰逊丑闻引起国际田联和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人的关注之前。
约翰逊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并不仅仅在于这位“世界第一飞人”药检出了问题。真正严重的是,在随后的司法调查中,他和加拿大其他优秀运动员都承认: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服用激素类药物而没有被查获。此外,他们还证实了一个当时已经流传几年的传闻:运动员们正在使用像生长激素这种因目前找不到满意的检测方法而未被国际奥委会禁用的物质。
由于奥运会是举世瞩目的体坛盛会,奥运会兴奋剂检查中的阳性案例自然会受到新闻媒体超乎寻常的宣传,带来极坏的影响。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问题的政策,以及奥运会兴奋剂检查的示范作用,对世界范围内的反兴奋剂斗争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经历过1989年至1990年东欧的社会震荡,当西方所谓的“铁幕”被拆除之后,人们进一步发现了国际体坛上运动员滥用药物的证据。所有的人都怀疑过前东德运动员曾服用药物,但至今没有彻底弄清的是:国家卷入的程度和究竟涉及到哪些奥运会项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前东德在运动药物的研制和使用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汉城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为统一所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滥用药物运动员的处罚标准,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它还为减轻昂贵的法律诉讼费用而建立了体育仲裁法庭。由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已开始增加赛外药物检查的次数,一些兴奋剂管理方面的漏洞已经得到补救。
新问题和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包括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游泳联合会和国际举重联合会等在内的许多体育组织强化了反兴奋剂措施,许多国家也都加强了反兴奋剂管理工作,国际反兴奋剂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
1.不断更新药物检测的仪器设备,积极研究新的检测技术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一种价值60万美元、功能先进的高分辨磁质谱仪投入使用。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使用的设备相比,该仪器的检测灵敏度提高了3倍,可以检测出运动员3个月前服用药物的代谢残留物。
经过多年的研究,检测血液兴奋剂的技术也取得了突破。继国际滑雪联合会1989年首次在世界滑雪锦标赛上进行血液检查后,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也开始在滑雪项目中进行血液检查。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还使用了同位素质谱检测新技术。据悉,由国际奥委会和欧盟设立260万美元专项基金的关于生长激素(hGH)检测技术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可望在几年内付诸应用。
2000年8月28日,在历时几年的关于检测EPO新方法的研究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准在悉尼奥运会上进行血检和尿检相结合的EPO检测(既采用澳大利亚研究的血检EPO方法,也采用法国研究的尿检EPO方法,两种检测结果互相补充)。如今,无论是冬季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都包括尿检和血检。
2.强化药物检查,增加赛外检查(飞行检查)
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近年来扩大了药检范围,增加了药检次数。现在不仅所有的奥运会比赛项目都进行兴奋剂检查,一些非奥运会项目(如保龄球、武术等)的重大比赛也已开始实施兴奋剂检查,甚至在残疾人奥运会上也进行了兴奋剂检查。
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总署的一份调查报告称,1994年一年内,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中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等国接受药检的运动员都超过了800人次。尤其是一些世界著名运动员,被强制接受药检的次数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俄罗斯举重名将彼得罗夫,在1995年4月至1996年3月的一年里,受检8次以上;我国的优秀女子长跑运动员王军霞,在第26届奥运会前的一年里受检12次;加拿大男子100米跑运动员、1995年世界冠军贝利,在1996年的前7个月里(第26届奥运会前)受检多达20次。
赛外检查也为更多的国际体育组织所采用,成为反兴奋剂斗争的有力武器。国际田联和国际泳联赛外检查坚持得最好,它们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乘飞机前往世界各国进行突击抽查。例如国际田联1996年赛外检查尿样多达1500例,几乎涉及所有参加奥运会的知名运动员,90%的世界锦标赛奖牌获得者赛前都接受了飞行检查。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终于翻开了奥运会兴奋剂检查历史的新篇章——首次进行了赛外兴奋剂检查。随后,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除进行传统的赛内检查外,也沿用悉尼奥运会的做法进行了赛外兴奋剂检查。
从获得国际奥委会资格认证的20多个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所提供的统计数字中,也可以看出全世界每年尿样检测数量的增长:1988年47069例;1990年71341例;1992年87808例;1994年93680例;1997年106561例;1998年105250例。
3.法律纠纷日益增多,国际体育组织难以应付
20世纪80年代,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一般都“低头认罪”,或者找找借口,声称“误服”。但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被查出的违禁者不但矢口否认服用禁药,还纷纷找律师打官司,不是声称有人做了手脚,就是指责药检程序不规范,个别人甚至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使国际体育组织常常处于有法难依,执法难严的困境。
1994年,英国女子田径运动员戴安娜·莫代尔因尿样中含有超量睾酮而被国际田联禁赛4年。但英国田联却支持她上诉,声称由于尿样存放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中,细菌反应会改变尿液成分。结果国际田联不得不宣布取消禁赛,莫代尔还要求国际田联赔偿73.25万美元。另一个著名案例是美国田径运动员雷诺兹,他因兴奋剂检查阳性受到国际田联禁赛处罚,但他在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状告国际田联,说自己是无辜的。该法院不仅判他无罪,还判国际田联赔款2700万美元。
一些国际体育组织规定,对服用类固醇者禁赛4年,但这样的处罚与一些国家的民法和其他基本法有冲突。如欧洲民法规定,对此类罪错不可剥夺长达4年的工作权利。因此,违禁者往往会在本国法庭胜诉。面对日益频繁的诉讼,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在人力和财力方面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做出让步。例如,国际田联1994年用于打官司的诉讼费就高达400万美元。1997年,国际田联被迫将已执行了6年的首次服用第一类药物(合成激素、苯丙胺、可卡因等)禁赛4年的处罚改为2年。
这些事例充分表明了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对国际奥委会解决各种棘手新问题的决心和能力提出了挑战。
4.成立专门机构,统一反兴奋剂法规
1999年2月,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了世界反兴奋剂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着奥林匹克运动、联合国、各国政府、非政府机构、运动员以及医疗界的60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通过了《洛桑宣言》。被看作是向兴奋剂全面宣战的这次大会通过了《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和其它加强世界范围内反兴奋剂斗争的决议。
1999年11月10日,在国际奥委会的组织领导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在瑞士洛桑成立。国际奥委会为该机构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该反兴奋剂机构的任务包括实施和扩大赛外检查、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制订反兴奋剂教育计划、逐步统一药物检测分析和使用仪器设备的科学技术标准与程序,以及每年制定和公布禁药名单。
2003年3月3日,在国际奥委会的全力支持下,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主持召开了哥本哈根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在这次会议上,8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所有主要的国际体育组织,以支持一项决议的方式通过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该《条例》是第一部为所有体育项目和所有国家制定的统一反兴奋剂法典。这预示着由国际奥委会开创的国际反兴奋剂斗争又有了新的突破。
立场坚定,忠于职守
面对困扰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兴奋剂问题,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看法代表了国际奥委会的一贯立场,他认为服用兴奋剂不仅仅是欺骗,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在走向死亡。尽管在他的任期内,国际奥委会经过艰苦的努力也最终没能彻底战胜兴奋剂这个“体坛恶魔”,但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初衷不改,决意将这场殊死搏斗进行到底。
2001年,医生出身的雅克·罗格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上任伊始,他就声称要在其八年任期内,坚决进行“反兴奋剂战争”。果不其然,在其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的首届奥运会——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总共进行了1997例兴奋剂检查,这与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621例相比,检查数量急剧增加了200%多,创造了冬奥会的历史纪录。这表明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罗格上台后,奥林匹克反兴奋剂斗争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毋庸置疑,国际奥委会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它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忠实承担的职责,把奥林匹克反兴奋剂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 上一篇
下一篇 >